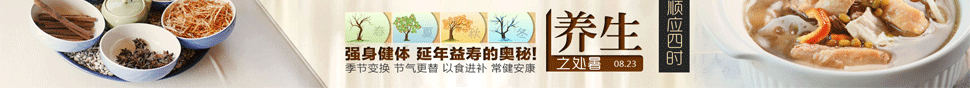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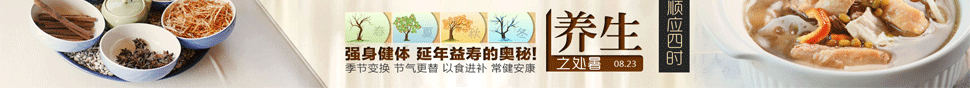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全民大搞中草药运动的时候,我刚上小学,学校里要求学生们课余采集中草药上交,这让城里孩子虽然新奇而热情高涨,但也很为难。原因是园林里不让采,精致的绿化管理也使得杂草不多;街边路角很干净,扫街的伯伯们会随手将杂草拔掉。另外,虽然那时候有院子、天井的人家还算多,但为要更多的生活空间,院子里搭屋建披的很多,砖是砖、石是石,没有空间给草生长。于是,大家放学后结伙去废空地、城墙边、土墩上。学校对采集种类是有要求的,我记得主要是马齿苋、鳢肠、地锦草、蒲公英、水花生之类,当然,老师们会先拔一些样品到课堂,教大家认一下。那时候不用塑料袋,学生们就用家里大人买菜用的竹篮,每天上学时将多多少少的草药带到学校。
我家有个长满植物的大院子,前院有用一块块切割成不规则的石块铺成的地坪,缝里长满了地锦草(Euphorbiahumifusa),小小的匍匐茎很多分枝,茎基常是淡红色的,叶背常是淡红色的,折断柔弱的茎,会涌出乳白色的汁液。马齿苋(Portulacaoleracea)被苏州人叫做酱板头草,长在房子墙根或草棵里,又肥又嫩,大人们还常常采摘或晒干,做包子馅或烧肉吃。后院的苦楝、枫杨林下草丛里,可以采到鳢肠(Ecliptaprostrata),这是一种菊科植物,头状花序外围两层舌状雌花,中央很多很多白色的两性花,等到瘦果长熟,一小盘一小盘就像缩小版的向日葵。地锦草、马齿苋、鳢肠(自上而下)院子里的蒲公英比较少,得到空旷些的草地里去找,虽然春黄花、秋飘絮相差无几,但中国有种蒲公英,大多分布西北、东北。仔细看江南田野里的蒲公英,叶片有深裂有浅分有全缘,但终究都只是一个种-蒲公英(Taraxacummongolicum)。蒲公英的嫩叶片也是可以吃的,极苦,近年来菜场时有见叫卖,据说很多人信它治病养生,但是微苦寒的特性,到底不是个可以当菜常吃的东西。东北来的同事常喜欢在工余时采一些,说是不炒不煮,洗净直接蘸大酱吃。蒲公英水花生(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,又叫空心莲子草),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三大猪草兼绿肥之一,其他两个是水葫芦(凤眼蓝Eichhorniacrassipes,又叫凤眼莲)、水浮莲(大薸Pistiastratiotes)。原产巴西的水花生,引种来后渐渐逸为野生,可长水中可生陆地,枝叶形态确实有些像花生,它和同样来自巴西的水葫芦,因为繁殖力旺盛,一发不可收拾,现在已经被列为外来入侵种。当年有个军事科研课题“”,也就是成就屠呦呦教授的课题,历时13年,60多个科研单位两三千人参加,我们单位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参加,除了抗疟疾植物的筛选,还延伸出其他主题如驱蚊、去腐生肌、疗蛇毒等资源植物的筛选研究,都是和战场用药有关的。水花生被筛选出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也是那个背景下,医院医院制剂使用过。水花生(喜旱莲子草)、水浮莲(大薸)水葫芦和水浮莲现在可是有身价的观赏植物。水葫芦叶柄中部膨大成囊状或纺锤形气室,黄绿色或者绿色,十分好玩。初中三年时光,每学年都会去农村学农,后来学校甚至在外跨塘造了一个学农分校,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月,边上课边劳动。农村常常会有胀满水葫芦绿棵的池塘,路过就悄悄蹲在池边,把一个个气囊捏瘪,所以也是曾经顽皮过。水葫芦开花很惊艳,穗状花序具9-12朵花,花冠6枚,最上面一片四周淡紫红色,中间蓝色,在蓝色的中央有1黄色圆斑,凤眼也!其余各瓣紫蓝莹莹,透明欲滴。水浮莲,飘浮水中,一丛长长悬垂的须根,叶簇生成莲座状,佛焰苞白色,干净得让人清净,真有些佛性。居然从不知晓它是个天南星科植物,只是在水缸或水石盆景中飘上几朵,每天看几眼,心收而神凝。
水葫芦(凤眼蓝)乙型脑炎、甲肝、流感盛传的时候,很多地方会架上大锅,煮些草药当药饮,分发给大家防疫抗疫,除了耳熟能详的板蓝根、金银花之类,还有一种当年也很出名的草药叫贯众,但不太记得它是应付哪种流行病的。《中国药典》上收录了3种贯众类药材,一种叫“绵马贯众”,基源植物是粗茎鳞毛蕨(Dryopteriscrassirhizoma),一种叫“绵马贯众炭”,其实就是第一种药材用炒炭法炮制而成;还有一种叫“紫萁贯众”,基源植物为紫萁(Osmundajaponica)。粗茎鳞毛蕨和紫萁都是蕨类植物,前者产东北、华北,后者产自山东开始,南达两广、东自海边、西迄云贵川、北至秦岭南的广大地区,故而正好是一北一南覆盖,加上两者的功效差不多,均为苦微寒的清热解毒、杀虫、止血,所以在疫毒来临之际,几乎全国各地均有地产而随手可取煎煮大汤的贯众材料。
粗茎麟毛蕨和紫萁粗茎鳞毛蕨我没有见过,但是紫萁在江南各地的丘陵地带随处可见,宜兴人呼之“薇菜”,前几年和泰华镇的一家企业合作时,见过他们将紫萁嫩芽盐渍处理,然后出口日本。《诗经》之“采薇”,吟哦美胜,按照许慎《说文云》:“薇似藿,乃菜之微者也”,因而如今大多数学者考证“薇”是豆科野豌豆类。然,纵观古代诗词,你会发现“薇”常常与“蕨”相连,如孟郊“野策藤竹轻,山蔬薇蕨新。”曾巩“老哺薇蕨西山翁,乐倾瓢水陋巷士。”赵秉文“遥知西山下,烟雨薇蕨长。”等等,这里描绘或歌吟的对象又应该是蕨类植物,元代刘诜《后采薇歌》曾描绘曰:“春采薇,婴儿拳。冬采薇,潜虬根。”这正是蕨类植物的形态无疑。故而,若“薇”是蕨类,那在江南,一般认为就是紫萁属的植物了。
蕨类植物的嫩叶及孢子囊《史记·伯夷传》说“食薇”的故事,伯夷、叔齐因抵死不食周粟,“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。”每天烤薇菜、做薇汤、调薇羹、制薇酱,可是有一天被村妇告知,那些薇菜生长在周王朝的土地上,其实也姓周,于是他们只能饿死了。王冕曾诗曰:“君不见孤竹夷齐久寂寥,首阳薇蕨今荒草。”看来首阳山的“薇菜”还应该是紫萁,只是由于野豌豆和紫萁均是广布植物,究竟是哪个?只能等待更多的证据了。野豌豆古人云∶“百头而以一贯,故名贯众。”亦有曰∶“根具百头,独茎叶两两相对,若偶贯群阴也,因名贯众。”春天,乘着时时有的润无声的细雨,紫萁短树干状稍弯的根里,嫩叶一片一片错落冒出,初出褐黄毛茸、卷曲如拳,也像是一个个大写的问号,询问贪食的人们何以下手撷嫩。不过三四日,嫩叶舒展,对生羽状叶生青发绿;再后来,孢子叶沿中肋两侧背面密生点点深棕色孢子囊;再后来,囊开孢子散,你看不见,我也看不见,它们去了土壤深处,孕育下一个生命周期。
不同种蕨类植物的孢子囊这些特殊时期的大汤,对于流行性疾病,究竟有没有用?还真的要等待一个一个实验及数据,经验必须立足于翔实的研究,真知必须来源于科学的证据。不过,不管人们存疑不存疑、争论不争论、使用不使用,草儿照常长,花儿依旧开,因为它们只有天时花令这一个指挥。注:文中所有图片引自网络或见原水印。悠家,修行草木之魂
悠家时光/草木集/悠家修心/悠家后院
联系:Hongxiutianxiangnj;hang-liuyueniu
六月牛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maboadw.com/mbjb/3818.html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