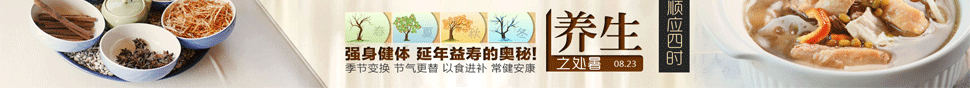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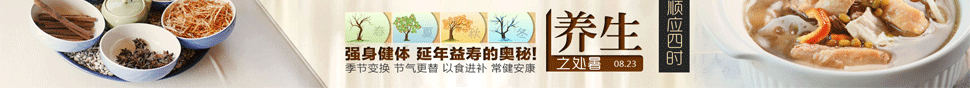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刘梦芙
近代名家诗词分论
近代诗词名手如云,这一部分中分别论述几家作品。黄遵宪是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,也是对二十世纪诗坛有重大影响的诗人,笔者重点辨析“诗界革命”属于文学改良,并非“五四”时期全盘否定传统诗文的“文学革命”;论证黄遵宪的思想品格由儒家文化陶冶而成,立足传统,融纳西学,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诗歌史上起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。另一篇文章专论黄遵宪的海外旅游诗,展示作者开阔的胸襟和诗中的新境界。邓秋门是青年早逝的天才诗人,文廷式是支持戊戌变动的大词家,文中论述他们的作品,见其爱国情怀。论易顺鼎的山水诗,可见诗人横放杰出的才华和自由超逸的个性。近代著名诗人如王闿运、陈三立、郑孝胥、范当世、樊增祥、丘逢甲、杨圻、赵熙、许承尧、金天羽等;词人如王鹏运、郑文焯、朱祖谋、况周颐、黄人、王国维等,二十世纪初至民国间皆在世,对“五四”后诗词深有影响,本课题时间有限,未能一一专论,日后将继续研究。
1、黄遵宪思想与“诗界革命”论衡
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,他游历日本、欧、美,归国后大力宣扬日本的明治维新及西方的民主制度、科学文化,积极参加戊戌变法,广结同盟,贡献重大。他平生功业多方,集政治改革家、外交家、日本史学家、教育家于一身,虽以诗为余事,但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在黄氏生前,其诗作就获得同代各派诗人的美誉;身后百年来,他更成为研究的热点,但其基本理路是,各种文学史及近代诗学论著无不言《人境庐诗》与黄遵宪的“诗界革命”,并将之视为一个核心问题和基本出发点。笔者认为,前辈学者如汪辟疆、钱仲联、钱钟书等对黄遵宪的认识多有真知灼见,但时贤后学之文,却每作空言套语,甚至厚诬曲解者触目皆是。本文详陈己见,以便澄清黄遵宪研究和学术文化思想的若干误区。
一、不言与滥言“革命”的原因与教训
由于梁启超在《夏威夷游记》中首标“诗界革命”,又于《饮冰室诗话》中张大其说,以黄遵宪为典范,推之为“近世诗家三杰”之首,其作品可称“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”,后人遂将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康有为、夏曾佑、蒋智由、梁启超乃至丘逢甲诸家统归为“诗界革命派”。于是,多种论著皆不加细察,视黄遵宪为“诗界革命”最早的倡导者。实则遍检黄氏著作,仅有“别创诗界”之语(《与丘菽园书》)及《酬曾重伯编修兼示兰史》中所谓“读我连篇新派诗”,而并无“革命”之说。黄霖先生云:“黄遵宪至死不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,处处讳言‘革命’两字,故他自始至终一直没有附和‘诗界革命’的口号”。他又引公度晚年与严复书云:“公以为文界无革命,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”。“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‘诗界革命’的明确态度,既反对严复的顽固立场,也反对梁启超的激进提法,而主张用‘维新’两字来概括当时诗歌及整个文学的革新运动”。黄遵宪有志于变法,同时正从事诗歌的创新,为何又讳言“革命”?黄霖先生说,他“对于革新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不够鲜明、直接和大胆”,“这或许与他在政治改革运动中一直采取‘潜移’、‘缓进’、‘蚕食’等比较稳健的立场有关”。[1]此说虽道及黄遵宪对待政治和诗歌革新的态度和方法,但未能探其思想本源。黄遵宪其实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特性有深切的理解,思想之成熟远越梁启超、谭嗣同等青年后辈,无论是诗歌创作或变法实践都是如此。
“革命”一词,《辞源》释曰:“实施变革以应天命。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,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。《易·革》:‘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,革之时大矣哉’!……今谓社会政治、经济之大变革为革命”。“革命”有广义狭义之分,当代学者李新指出:“从广义上说,也就是从哲学意义上说,即凡是引起质变的事物都叫革命。或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,就是变化比较大、斗争比较激烈的都叫革命。从语言学意义上讲,革命还可以当形容词,凡是正义的、进步的都叫革命”,如宗教革命、工业革命、农业上的绿色革命等等。“历史上的一些正义行动,也往往称之为革命”,如奴隶起义。“从狭义上讲,是专指社会科学而言,比如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,等等”,“这种革命指的是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。……严格地讲,革命必须包括两个条件,一个条件是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。另一个条件是,必须通过暴力,通过激烈的斗争,或者是一场暴动,或者是一场革命战争。因为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,虽然改变了社会性质,但不叫革命”,如日本的明治维新、俄国的农奴解放,政治制度是自上而下改革的,虽然改变了社会性质,但未曾使用暴力,“因此,革命要有第二个条件”。“改良是与革命相对而言的,革命是暴力,激烈的行为,而改良则是渐进的。在革命胜利后,我们就要用改良的办法来达到革命的目的。”[2]
梁启超主张的“诗界革命”属于广义上的一种文学革命,要求“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”,即输入“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”,但旧有的诗歌形式不变,所谓“革命者,当革其精神,非革其形式”,实质上是一种改良。而发生于“五四”前后的新文化运动,以激烈的方式批判传统文学,废除文言文,打倒旧体诗,斩断千年承传的文化血脉,所创建的新诗从内涵、语言到表现形式都与古典诗词迥然不同,这是一种狭义上的革命。黄遵宪虽然也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观念,积极参与政治改良,以诗歌宣传维新思想,但在深层心理中仍不离中国文化传统,对于“欧洲之真精神”只是有选择地汲取,不走“全盘西化”之路。因此他避“革命”之名,行维新之实,政治家的稳健作风亦表现于诗歌创作中,不守旧亦不激进,在推行新政和诗境更新两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绩。
黄遵宪足迹遍中外,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极为干练的行政才能,是知行合一、脚踏实地的改革家,在维新志士中非常罕见,康、梁等人远不可及。他长期考察日本、英、美各国政治制度,多方参较,于中国变法应采取的措施、步骤熟虑于胸,到湖南全力协助巡抚陈宝箴厉行新政:举南学会、开时务学堂、办《湘报》,首倡地方自治,创立保卫局,“分官权于民”,一切计划均由黄遵宪筹措并付诸实施,井井有条,步步到位。湖南风气因之大变,成为全国注目的改革典范,黄遵宪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。此外如在日本期间拟《朝鲜策略》,有深谙国际政治的战略眼光;在美国、新加坡任领事时善于运用法律知识以维护华工、华侨的权益;在国内处理多年积压之教案,折服洋人,无不显示出其超人的魄力和精细明敏的实干作风,既能为循吏,更能为贤相,李鸿章称为“霸才”,绝非过誉。后人总结戊戌变法失败,有多方面的原因,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光绪帝所任未得其人。正先所撰《黄公度》云:“戊戌维新运动,在湖南所以成功,因陈宝箴、公度等,都是政治家,资望才学,为旧派所钦重。凡所措施,有条不紊,成效卓著。反对者虽叫嚣咒骂,而事实具在,不容抹杀。在北京所以失败,因康有为、梁任公等,都是言论家,资望不足,口出大言,而无实际,轻举妄动,弱点毕呈,一百日间,竟为光绪下变法特旨三四百道。及光绪觉悟康有为之不足恃,以驻日本钦差大臣之职予公度,而不予有为,三诏严催公度攒程赴京,以图挽救,而时机已失,京变作矣”。[3]彭精一先生亦云:“公度先生能于百年前即有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之思想,此种思想,实得来不易,先要以自己国家、国情、人性、风俗结合先进国家立宪法、国防、外交、议会等制度,然后使可行者融贯之,不适行者则缓议之。例如后党当权,光绪羽翼未丰,设谋者坚以太后归政光绪帝,只知道名政,不知权力之所依,每事以实力为后盾,如此良策未定,乱步先行,而致以卵击石之结果。……若光绪选用公度,则公度将察情度势,劝光绪上结慈禧以善母子之情,厚母后亲信以顺光绪变法施政之道。假以时日,则母子慈孝敬爱,于时施政变法,得权力而后为,岂不顺流无阻,上下畅通乎?”彭先生复以谢安用“和靖以应,结交以防”八个字,战胜桓温、中兴东晋为例,“这个故事比之康有为之‘百日维新’,轻信袁世凯,殊发人深省矣”![4]这些论断都切中问题的要害,为光绪未能及时重用黄遵宪而深致惋惜。但今日学者分析变法败因,以为是:〔一〕变法领导者不掌握实权;〔二〕改良派不敢和不能摧毁封建制度,反映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;〔三〕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;〔四〕缺乏完整、科学、行之有效的变革理论;〔五〕缺乏全盘考虑,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。[5]。上述原因固然有其道理,但论者既未将湖南新政与北京施政结合起来通盘考察,又未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maboadw.com/mbjb/4917.html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