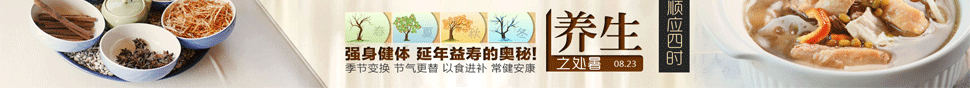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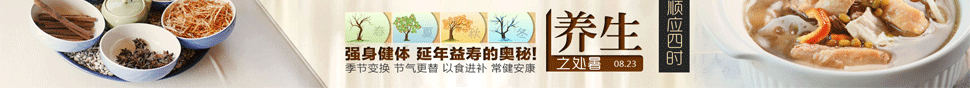
富顺的坊间,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,一个关于盐井街的传说。那时,人烟稀少的富顺地区,有个年轻人叫梅泽,出外打猎,发现山脚下有只鹿子,正在贪食从石缝中流出的泉水。他搭箭拉弓,鹿子仍然不愿离开。他觉得奇怪,跑过去捧起山泉,尝到是咸的。于是,梅泽就在这里掘井采集卤水,熬制成盐。很快井盐生产就漫延到周围团转,逐渐吸引了一批手工业工人和贩夫走卒,成了一个人群聚集地。人们因盐而获利,就把最早开凿的盐井称为“富世井”。后来为了纪念梅泽,人们尊崇他为盐神,就近修庙供奉起来,以护佑盐井的长久兴旺。相传那座小小的庙宇,就在今天的盐井街口左边石坎上。老一辈人说,民国时扩建街道,那座破旧的庙子才没有了。
历史记载,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,蜀郡守李冰,已在四川开凿了盐井。生产地域慢慢扩大,遍布四川东、南、西、北,久而久之,由于种种原因,许多盐井渐渐枯竭,盐场倒闭。唯有川南富顺一带的盐井,仍然生生不息,独自火红。
富顺是古代江阳(今泸州)的一部分,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,才划出富世盐井周围地区,设为富世县。自隋唐至明清,几经演变,由富义县、富义监、富顺监、富顺州,至今天的富顺县。就是说,从古江阳划出富世盐井地区,设立县,产盐的富顺历史,已经有一千多年了。
县志上说,隋唐时,富顺的盐业十分兴旺,闻名巴蜀。到了明末清初,卤源逐渐稀少,便向西沿釜溪河寻找。相继开采出邓井、太原井、王井和张井等,最后在火井沱浅石滩一带开了新井。此井并非人工开凿,是因卤水自然流出,而流量颇大,故名自流井。
人们提起盐,就会想到四川盐都,想到名闻遐迩的盐都自贡市。其实,自贡是三十年代末才诞生的一座新城市,它原属老县城西北一个产盐的自流井区,年划出,与紧邻的贡井区合并,成为自贡市,也是因盐设市。无论声誉如何,只有几十年的历史。用老百姓的话说,寻根问祖,仍离不了千多年的老县城富顺
毫无疑问,老县城西的盐井街,就是当年富世井的遗址,离西门外我家“怀远号”不远。自小,我就耳闻不少有关盐的故事,盐神菩萨,盐与豆花,陕娃与邓井(关),盐担子与翘扁担,以及自流井,盐帮办学(支持邓关小学和创建平澜中学),盐帮献金抗日;目睹盐担子、马驮子,三元宫盐市坝、过秤的码门口、西湖口的马掌坝,邓关大河街河边靠的一溜盐船,盐商与西秦会馆等等。
20世纪50年代的“大跃进”,以及90年代初的城区改造,在盐井街地段,先后发掘出不少古时烧盐的遗物,输送盐卤的石枧槽、灶门、灶圈和盐锅,又在盐井街上面的田家祠堂,即今少湖酱园厂,及周围的民房地段,发现几个废弃的盐井,印证了史书上记载最早产盐的富世井,就在这里。
过去的盐井街,从街口往上到少湖,几乎没有商铺。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,短短几百米长的一条街,大多是青瓦白壁的居民住户,十分清静。临街是双扇大门,两边有小木格十字窗户。街边的大门外,还有腰门,是三四十年代常见的民居格式。中间那一段房屋,檐高敞亮,门外檐坎上,常睡着晒太阳的猫。看来房主较为富有,住的人户大多姓张。其中一家叫张在田,与我父亲同在女中教书。据说他家在乡下有地方,土改时房地产全部没收,扫地出门,不得已搬到我们怀远号弃用的晾房栖身。他的儿子张学元和张二娃,是我的同学和发小。一个十分斯文,一个极其活跃,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那时盐井街不宽的路面,铺的是方石板,除了稀少的行人,偶尔有人力黄包车跑过。大概因地势关系,街边房屋地基稍高,进门要上两三级石梯。40年代县城的文化名人严逸耆老先生,就居住在盐井街,我小时曾经跟随祖父去过他家,记得清楚门口也有石梯。靠考棚外墙一边,除街口几家进深有两间,往上房子的进深浅了,仅一两间而已。再往前就没有房子了,只见考棚的高墙。街上头,隔着田家祠堂,就是少湖了。我儿时的老同学谢又清、牟祖佑和邹永泰,以及邹联龙的家,就在这一带。
盐井街几经风雨,今天的模样,与当年已大不相同。石板街道拓宽了,铺上沥青塑胶混合的路面,黄包车没有了,来往的汽车不断。街道两边那些黒瓦泥墙的低矮房屋,变成了七八层高的钢筋水泥楼房,底楼全为商铺,木板门和腰门换成整齐的卷帘门。散居地面的芸芸众生,全住上楼房了,那是早些年深,人们有幸过上了口头念得很顺的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的美好生活啊。
盐井街下面的大片低矮的旧房屋,直抵城墙和西城门洞,已全部拆迁,城门早在50年代初就毁了,连城墙也铲平,90年代,修起了一排楼房。这片宽阔的街面上,只留下中间两棵高大的黄桷树。以黄桷树为中心,,建了一座“古井咸泉”的醒目地标。台阶上立了高高的天车井架,并镌刻了碑文,由时人刘海声撰写,肖尔诚书,命工匠将古老县城产盐的画面,勒于石上,让后人继往开来,发扬光大。当局把此地命名为“梅泽花园”,可大家都顺口叫成“黄桷树”。
今日的梅泽花园,是新老城区的交汇处,已成了全城最热闹的地方。周边高楼林立,楼下的商铺琳琅满目,街上的人如过江之鲫;公交车穿梭往来,拥挤着私家车和出租车,一天到晚,热闹纷繁;一排的豆花饭店和散布周边的羊肉馆、牛肉蒸笼、面包坊、小吃铺,迎送着络绎不绝的客人。手机和电脑行,星罗棋布。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大楼,耸立在西城门遗址的两旁,与西门外的农行和工行遥相呼应,管控着县城的金融流通。更有刚建成的地下商城,以梅泽花园为起点,沿通往西门的街道下面,上千米长,如一条新颖别致的地下画廊,吸引着无数观光的人群。地下商城冬暖夏凉,地面全铺的是整齐光洁的地砖,顶上是弧形相连的霓虹灯光,商店的货物充盈,穿戴时尚衣帽的大小模特儿,摆着姿态,招徕顾客。那些晶莹闪烁的儿童商店,犹如阿里巴巴的奇异宝库,吸引了儿童的眼光,更让小宝贝们流连忘返。还有长廊尽头的旱冰场,青少年们平常尽可游玩,节假日分外拥挤。这个明亮的地下商城,在非常时期,又是躲灾避难的“人防工程”。
从盐井街口往东,新开了一条横穿老县府的街道,直通码门口。北可去西湖塘,南到小南门,出城门有水码头,据说以前出产的盐,就在此装船运往各地。老县府已卖给了开发商,周围住户全迁走,新修了远达小区和远达商城。新街道两边楼底,全是商铺,什么波司登、森马服装、南洋百货商城、阳光眼镜行、富洲大药房,还有专营化妆品和金银珠宝首饰行。
不少店家放着音响,顾客盈门。每当天晚,商铺内外灯火辉煌,夜市开始了,街边摆上挂满了时尚服装的衣架,挤着各种小食水果摊。川梭不息的游人,满街热闹非凡,比白天更繁华。
千年古县富顺,随着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历史上,积淀了无数的人文景观。红墙黄瓦美轮美奂的文庙,是县城香火鼎盛时期的九宫十八庙的龙头;荷叶田田秀美的西湖塘,自是富顺十景中的耀眼明珠。吸引了历代无数的名人雅士,墨客骚人,竞相吟出数不胜数的诗词歌赋,为其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不已。
黄桷树周围,至今尚有不少文化古迹依稀可寻。
盐井街右边的万寿宫,四周是雕花拱形的风火高墙,厚重的大门斜开在当街,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坝子,不时有跑江湖玩猴子的,耍杂技的、卖狗皮膏药扯把子的,在此招揽游人。进大门是台口向内的戏台,面对一个石板铺就的大坝子,上高梯坎就是宽大的正殿了,那是我们读书时的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。戏台和正殿上的雕梁画栋,随着岁月的流失,色彩虽然已经暗淡,却仍十分生动。万寿宫原是江西人的会馆,继后又成了学校。我记得校名“西城小学”前有“赣省”二字,不懂是何意,后来学了地理课,才知道是指江西省。赣,是江西的简称。这个会馆,不知是否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有关。那个笔画多的繁体字“赣”,本来很少见,更不好写。我曾和几个同学,为这个字究竟有多少笔画争得面红耳赤;与同学玩写字游戏时,比赛谁写得快、写得好。结果我写的乱七八糟一大堆,赶不上同学牟祖佑写的中规中矩,紧爪(富顺方言,收束得当)受看,被围观的同学嘲笑为“一堆灰包”。因为“赣”字戴在学校头上,倒叫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繁体字。我就是在这里发蒙和受完小学教育。50年代,西城小学迁到半边街,这里成了县武装部。随后,逐一拆毁了庙门、围墙、戏台等老建筑,修了几栋楼房,四周种上花草。万寿宫变成了政府机关。到了90年代老城改建,武装部又迁走,开发商进行重建,修了一栋挨一栋的楼房,住满了人户,取名“黄桷树小区”。万寿宫就此彻底消失了。
西门外有个三元宫,在米行对面。一条小巷进去,原一中校门一側,庙子规模不大,供奉的是道教的天、地、水三官菩萨,由一个脚跛的矮小道徒守护。难怪每年端阳划龙船后,西门码头的黄龙船,就存放于后殿,由水官管制。40年代三元宫前的石板坝子,还是盐巴批发地,左边的几间屋子,是盐仓库,楼上住的是那个道门儿和他的徒弟。大约在60年代,三元宫成了富顺一中的生活区(伙食团)。几经拆建,完全变了,至今,三元宫与万寿宫,同样灰飞烟灭了。
米行(今天大家叫猪市坝)右边,临江有独立一峰,山顶的玉霄观,常年香火不断。每当太阳落坡,形成了县城有名的风景“凌峰夕照”。那景致,一定光鲜靓丽过不少年月。如今,已破旧衰败,不免使人感叹“人老珠黄”,被周围栋栋楼房遮掩,不显山不显水,矮踏踏一个山包。连山门左边石柱上的对联,也被乱搭的民房挤得看不见了,只有右边依稀可见“万里波澜扫海图”字样,不知被遮的下联,是“千仞高峰凌云志”么?以前四面房屋低矮,玉霄观自然突兀江边。山门前是迎江的石梯,到半山腰倒拐,顺山脚而下。炎炎夏秋,当夕阳缓缓坠落,倦鸟归林,山水光色迷漫,使人自然想起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多么赏心悦目。随着岁月的风吹雨打,玉霄观到50年代,已沦落为贫穷的居民大院。如果今天能迁走拥挤的住户,将破旧庙宇修整一番,仍然可供人们劳作之余游览观光。
值得提及的,是与盐井街一墙之隔的“考棚”,即明清时举行科举考试的试院。80年代改革开放前,一直是县府所在地,科举考试时的考场保持得很好。进大门,穿过大坝子,上梯坎就是一个树荫笼罩的安静大院,两边各一排平房,分隔成一间一间整齐的考试小屋。无论是民国时期做小学的课堂,还是解放后作县政府时的各科办公室,都保持了原有的样子,是至今唯一留存下来最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。但这样一个可供直观的历史文物,在90年代城市改建中,却被那些被金钱迷惘而数典忘祖的不孝子孙毁掉了,真是太可惜.
更值得一说的,是富顺名人陈铨,他的故居就在盐井街附近。离“考棚”左边不远,以前有一间“同兴和”中药铺,里面有个院子,那就是现代文学家陈铨的老屋。三四十年代,名噪一时的陈铨,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,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教授。年他在清华读书时,就写了长篇小说《天问》,一举成名,受到朱自清和吴宓的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maboadw.com/mbfb/5823.html


